刘家和:清代的学术
- 文学
- 2025-04-11 11:22:08
- 10
本文摘自《困学卮言:史学家刘家和先生的学术和生活自述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25年1月,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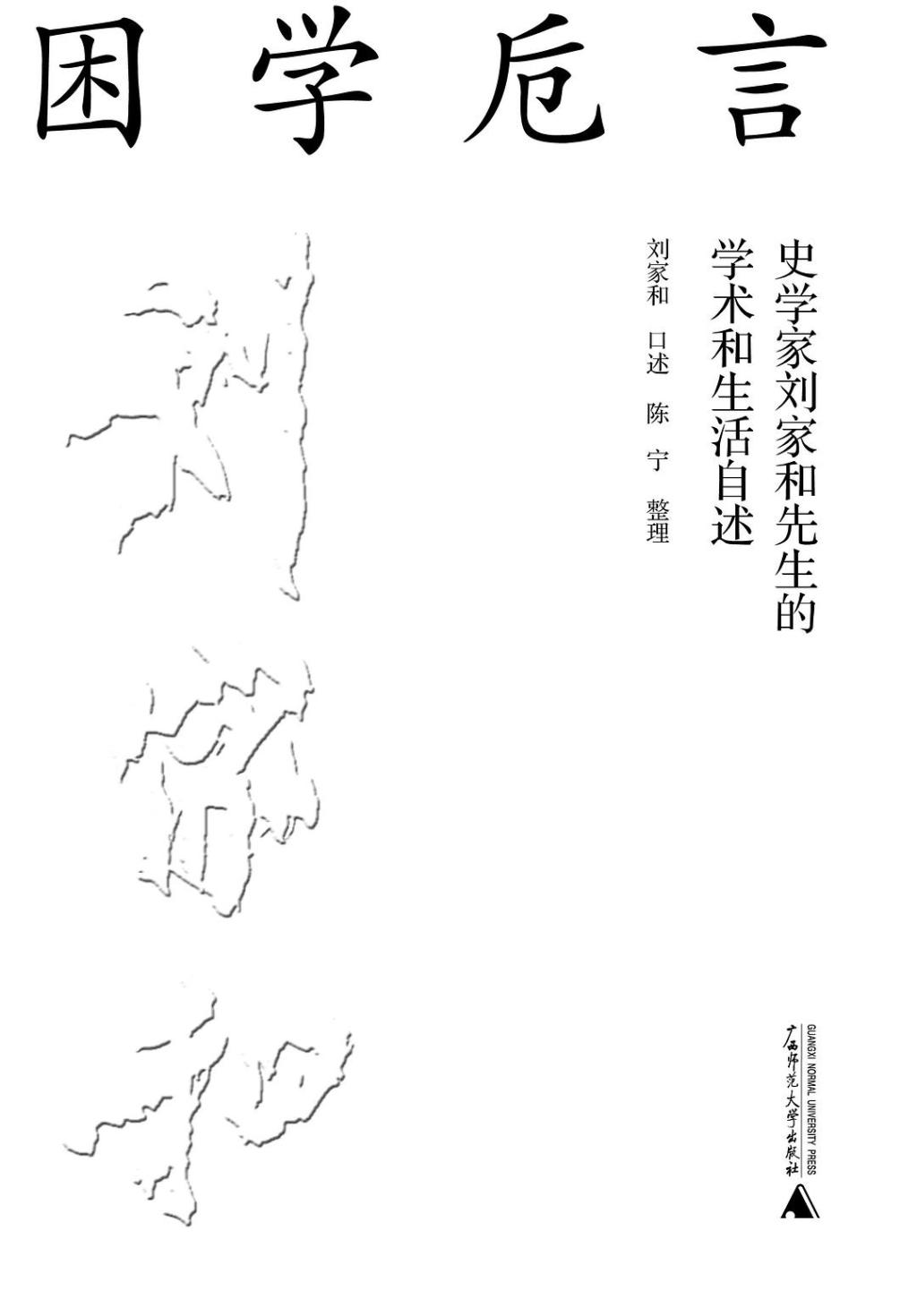
我住在西单附近的时候,曾经每天黄昏去逛旧书店,或“蹲书摊”,作为休闲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非常关注清代学者的年谱,每遇到这类书,总要翻看,甚至重复看。通过阅读他们的掌故,我对清人的学术研究以及目录学有了深一层的了解,这些知识深化了我的研究工作。
清代大学者的著作,都有人做过校对。校对者不是普通人,而是大学者的高足。让弟子承担校对,就是培养后继之人的过程。
《尚书》中的《汤誓》可以认为是真的,《汤诰》是伪的。凡是司马迁看到的先秦文献都算是真的古文,是春秋时期的人根据口传整理出来的。王引之的《经义述闻》和俞樾的《群经平议》对读《尚书》非常有帮助。王引之的分析让人读起来最“过瘾”,俞樾的评议还有些穿凿。
章学诚自称不讲门户,实际上他最讲门户。现在对章学诚评价太高,不太符合实际。他是个悲剧,他看到清王朝的弊病,有心改变,但学问不够,还很自负。他的思想远不如王船山,与西方学术更是无法相比。当时康德的历史理性理论已经出来了。
戴震对章学诚说,他对理学很反感,因为它束缚人性。章学诚认为戴震是两面派。戴震说,学问有两种,一种是抬轿子的,一种是轿中人。你们只看到我做抬轿子的学问,你们不知道我是坐轿子的人。……戴震五十四岁去世。
崔述(崔东壁)是辨伪大家,非常自信。他怀疑一切,只相信“六经”(其实是五经),经以外的传,一概不信。他重视客观证据,决不凭主观成见,人云亦云。他在《考信录》里提倡学者要有“老吏决狱”的能力,一眼看出问题所在,这样的能力,就是先见。我们既不能缺少先见,也不能为先见所障蔽。
崔述在《崔东壁遗书》中说,他小时候,他爸爸让他读书,每本书读一百遍,然后再让他背。这样就把书的内容记得烂熟,所谓“读书百遍,其义自见(现)”。其实,在理解的基础上背,效果会更好。
廖平的学术被称为“六译”,我只读他的前四译,后面的两译是有关谶纬的。
人生,不能以现在的地位高低来衡量成功与否,每个人有自己的性格、自己的活法,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最重要。清代很多学者都说明了这一点。很多有学问的人,都是从官场退下来之后取得学术成就的。赵翼被派到广西去镇压暴乱,他办了主犯,放了从犯,结果遭到降职。他因此借故辞官,回家养老母。从四十四岁到八十八岁去世,每天读《廿四史》,做功课,很消遣。钱大昕、王鸣盛都有类似的经历。他们这些曾经做过高官的人,在地方上无人敢欺负,经济条件也很好,可以专心读书。
阮大铖是明朝末年的佞臣,清人入关后去世。南明之所以灭亡,有一大原因就是像阮大铖这样的小人当政。但是,这个人也是一位文学大家,著有《燕子笺》和《春灯谜》等戏剧作品。我清楚地记得牟宗三先生给我们讲的有关阮大铖的故事。阮大铖小时候,笨得要死,还贪玩。他家里有钱,请老师在家外一间专门学习的屋子教他。不管教他什么,他都学不会。中午休息,老师趴在桌子上打盹,他就溜出去玩。有一天,老师生气,打盹时,把桌子移到门口,堵住了门。他很笨,不知道从桌子底下钻出去,就只好在屋子里等老师醒来。老师和家长都认为这孩子没出息,学不出来。有一天放学后,他没有回家,家里人很着急,直到月亮出来了,他才回家。家人问他干什么去了,他说作诗去了。他爸爸嘲讽地问,你能作什么诗?他妈妈说,你让孩子说。阮大铖就说,他在路上看到池塘边有人用罾(罾就是有十字架支撑的网,将它放在水中,看到鱼虾进入网区,立即扳动罾,捕获鱼虾)钓虾。他说他只写了两句,第一句是“虾子鱼儿无一个”,他爸爸一听就气坏了,骂儿子写出这样的烂诗。他妈妈鼓励他说第二句,儿子说:“只扳明月两三罾。”这是写人们在钓月亮,比起钓鱼虾,境界高多了!父母对他顿时刮目相看。从此以后,阮大铖开窍了,后来在文学上越来越有成就。
惠士奇在广东做官时,广东天气热,但他白天都要穿着官服,戴着纱帽。一下班,把门一关,脱去官服,光着膀子,开始背《汉书》。他的学生在门外听着。惠士奇很投入地背,一遍一遍地背。这样的功夫,看起来很笨,但背到一定程度,脑子里的东西足够多了,人脑就变成了电脑,效率就来了。检索速度很快,联想能力很强。有效率必须要有联想力,看到一个东西能够很快联想到其他东西。效率来自多方面的准备,来自多方面的训练。读书如果能够“里应外合”,就能提高效率,这也是知识结构的问题。同样是看人“扳罾”捕捞鱼虾,你如果有多方面的积累,当接触到新材料或者读到别的书时,你就能够里应外合,就像阮大铖说的“只扳明月两三罾”。
清人在目录学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。对治史的学者来说,掌握目录学知识是必要的,近代学者非常注重这方面。邓广铭先生曾指出,治史学有“四把钥匙”:年代、历史地理、职官制度、目录学。其中目录学是搜集史料的门径。邓先生受教于陈垣先生和傅斯年先生,他的观点肯定受到两位老师的影响。陈先生是史料学大师,傅先生更强调:“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。”傅先生的观点有点偏激,史料毕竟不同于史学,二者应该分开,但强调史料对于史学的重要性是对的。做学问要从学习目录学开始,学目录学,不能不读余嘉锡先生的《四库提要辨证》。余先生在读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时,发现其中有很多错误。这些错误也许是《四库》的编者们因乾隆急于成书而草率不求精所致。余先生在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中纠正了他所发现的错误。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也从别的方面补足《四库全书》的内容。张之洞此著是为了回答年轻人应该读什么书的问题。近人范希曾作《书目答问补正》,纠正原书的错误,又增加了张之洞以后一些书的新版本。值得注意的是,《书目答问》有《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》附在正文后面。姓名略为什么重要呢?孟子说:“颂其诗,读其书,不知其人,可乎?”(《万章下》)姓名略记录了一些有关著述家的掌故,给读者提供“知其人”的背景材料。除姓名与流派以外,姓名略还介绍了其他方面的内容:有些人没有著作传世,但其论述散见于他人著作中;有些人不专一科,兼治经学、史学、小学;等等。
孟子提倡的“颂其诗,读其书,知其人”尤其受到明清两代学者的重视,王世贞的《弇山堂别集》,黄宗羲的《宋元学案》(黄未做完,全祖望接着做),李集的《鹤征录》(李集未完成,其子李富孙、李遇孙续写),江藩的《汉学师承记》《宋学渊源记》等,记载了大量的掌故。近代学者柴德赓的《识小录》与其他文章,也以掌故为主。通过这些掌故,我们可以了解著述家的知识结构、学派传承,著述的背景,以及他们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,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他们的学术观点。
乾嘉学派中,吴派的惠周惕、惠士奇、惠栋祖孙三人成绩斐然,但三人的思想却不同。惠周惕思想比较保守,维护清廷的统治,学术上尊汉学也尊宋学;惠士奇和惠栋政治上有反叛倾向,学术上反对宋学。江藩的《汉学师承记》和钱大昕的《惠先生士奇传》记录了一些他们的掌故。雍正针对官员的贪腐设计了一个方法,名为“宰肥鸭”。他在官员贪腐到一定程度时,或没收其家产,或令其自费修城治河。惠士奇在广东做学政,名声很好,但返京后雍正令其自费修镇江城。惠士奇散尽家产修城,资金仍不够,没有完成,被雍正罢官,直到乾隆时才重新被任用。钱大昕认为惠士奇是被冤枉的。惠士奇的经历与他反宋学批程朱不无关系。江藩《宋学渊源记》记载,惠士奇(一说惠栋)将手书楹帖“六经尊服郑(服虔和郑玄),百行法程朱(二程与朱熹)”,挂在堂前柱子上,以表示尊崇汉学与宋学的立场。然而,这很可能是给外人看的,是护身符,并非惠氏本意。李集的《鹤征录》记录了惠栋惊人的记忆力,并赞赏他的名言:“宋儒之祸,甚于秦灰。”戴震、阮元等清儒都有批判宋学的言论,这是因为时代的变化,与雍正利用程朱理学杀人不无关系。戴震指出:“人死于法,犹有怜之者,死于理,其谁怜之!”阮元反对宋明理学对儒家经典的曲解,提出“古今义理之学,必自训诂始”的主张。
柴德赓先生研究清代学术和学人掌故,他认为:钱大昕处事小心谨慎,但他能与不可一世的戴震交往,因为二者都不满宋学。汪中与章学诚水火不容,但与钱大昕则关系很好,也是因为汪、钱讲经学常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而发。同样,钱大昕、汪中在著作中不提拥护程朱的章学诚,他们关系疏远,肯定与观点相悖有关。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·史德篇》中将谤君的人视为“名教中之罪人”。柴先生发现,“名教罪人”是雍正喜欢使用的字眼。雍正兴文字狱,年羹尧奉旨自杀。年案波及钱名世,雍正亲笔写了一个“名教罪人”的匾,令钱名世挂在自家门上,以羞辱之。章学诚使用“名教中之罪人”一词,明显是在维护“以理杀人”的礼教。柴先生明确指出:“了解一个人的思想,从议论上去找以外,还有无声之声,要在细心读书才能发现。”这里的“无声之声”就是指掌故之类。
想要了解古代都有什么书,大家都会从清人纪昀主编的《四库总目提要》入手。这部书的优点是有目有录,不仅有作者及其著作,还有作者生平介绍、著作内容评价;对不宜收入的书,只保留书名,略附提要,称为《存目》。其缺点是分量大,二百多卷,而且乾隆四十六年以后的书没有收入。后来纪昀又编了《四库简明目录》,缩减到二十卷,删除了《存目》。《四库简明目录》过去广为人知的只有两个版本:邵懿辰的和莫友芝的刊印本。后来黄永年先生在旧书店又发现了朱修伯的传抄本。朱本因此出版,由顾廷龙作序,黄永年写前言。这三个版本各有千秋,相互补足。
版本质量的高低,取决于注释者和校勘者的知识水平和学术水平。有些书不仅涉及的方面广泛,而且包含了非常专门的知识,比如《尔雅》。《尔雅》“释诂”“释言”“释训”解释字义,“释亲”“释公”“释器”解释亲属称谓和生活用器,“释地”“释丘”“释山”“释水”解释地理,等等。《尔雅》与《说文》不同,前者根据语境解释字义,后者不重视语境。清代学者研究《尔雅》的著作不下二十种,其中邵晋涵、郝懿行的注释是佼佼者(张之洞认为“郝优于邵”)。校勘四库这样的涵盖广袤的类书,没有多年的知识积累是不能胜任的。传统的知识结构中,许多部分是相关联的。比如,历法与天文,不知天文,就不知历法;历法又与音乐搭在一起(《汉书》有《律历志》);天文学(astronomy)又与占星术(astrology)纠缠在一起。这些有关版本的知识,学人不可不察。
清人朱一新在《无邪堂答问》中提出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,他指出,掌握目录学知识,所有书商都可以做到,“何待学者乎”。对书商而言,学习目录学为的是获得经济收益;对学者而言,掌握目录学为的是提高研究水平。如果不将目录学知识应用在学术研究上,学者与书商无差别。要研究,就必须要发现问题。从实质上说,目录学就是分类的学问,而分类的标准离不开逻辑学。中国历史以典籍浩瀚闻名于世,众多的典籍必然发展出图书的分类。我们可以问:中国古代的目录学是以什么为分类标准的?其分类标准是否符合逻辑?
中国古代对图书的分类,一直没有严格的标准,或者说缺乏统一的分类标准,从先秦到清代都有这个问题。从《庄子·天下篇》和《荀子·解蔽》对先秦诸子的评论来看,区分诸子的标准不在学科,而在学派,这样的分类很容易将不同学科的著作混杂在一起。汉代的司马谈继承了这一分类标准,他的《论六家要旨》更是认为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诸家的主旨是一样的,都是为了“治”。其实,从学科上看,这六家很不一样;从主旨上分析,各家也不尽相同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刘向的“七略”分类,即六艺、诸子、诗赋、兵书、术数、方技,外加目录。这样的分类大有问题,诸子类怎能没有兵书、术数、方技?当然,这与汉成帝的干涉有关。刘氏将诸子分为九流:儒、道、阴阳、法、名、墨、纵横、杂、农。这仍然是按照流派区分的。依据刘氏,诸子出于王官;诸子之分,在于他们所守或职能不同,而不在于学派的观点不同。因此,刘氏的分类,兼流派与职能,标准不统一。另外,按照职能的标准,刘氏认为纵横家“出于行人之官”,但是先秦诸子,除道家以外,无不周游列国,冀以被国君任用。对农家的划分也有矛盾,将倡导“君臣并耕”的思想流派之农家与介绍农耕技术之农家混为一谈,明显缺失标准。到了清代,分类标准仍然存在问题。《四库全书》将儒、释、道三家合并到子部,使子部类的书驳杂不一;还将先秦道家与汉代以后形成的道教混在一起,不合情理。这是根据什么标准分的呢?《四库提要》子部总序断称,“自六经以外立说者,皆子书也”,这意味着,史部、集部中全无立说之作。司马迁的“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如何解释?中国传统追求的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的“立言”如何解释?
过去研究目录学的学者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,但都忽略了目录学中的分类标准这一问题,这也许与时代的局限有关。今天我们学习目录学,应该与时俱进。严密逻辑是人们思维的正确方式,更是学者的必要工具。目录学,首先是分类;分类,首先是逻辑。我们做研究,必须将逻辑规则应用到方方面面,不止目录学。
清末的王闿运,科举出身,很会写对联。他曾经在曾国藩的幕府工作,活到民国。袁世凯死后,他写了副挽联:
民犹是也,国犹是也,何分南北;
总而言之,统而言之,不是东西。
还有一副:
男女平权,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;
阴阳合历,你过你的年,我过我的年。
上一篇:婚车后备箱创意装饰技巧
下一篇:澳洲工作签证一年费用解析











有话要说...